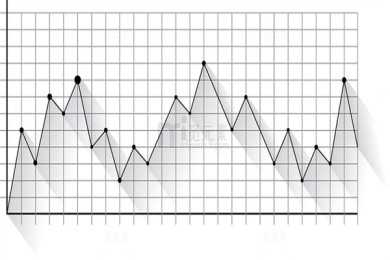远山近情
"咱村的人怎么都不来?"我看着院中空荡荡的场景,压低声音问母亲。
她眼眶通红,声音发抖:"你二舅一辈子做好事,临了却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
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有五,在县城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工人。说起这故事,还得从我二舅徐长柱的出殡说起。
那是八十七年的深冬,北风刮得院子里的黄杨树"哗哗"直响,墙头的积雪簌簌往下落,像是老天爷也在为二舅流泪。
我们几个亲人站在那座青砖小院里,看着那口薄皮棺材,心里比天还要凉。老式的煤油灯在风中摇曳,照得人影憧憧,更添几分凄凉。
二舅家的木头大门前空荡荡的,往日里该热闹的出殡场面,如今只剩下我们几个血亲,连个上前说句"一路走好"的邻居都没有。
"你二舅这辈子,真是受了委屈。"母亲掏出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擦着止不住的眼泪,声音哽咽。
二舅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五十岁出头,瘦瘦高高,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沟壑一样深。他一辈子没啥大志向,就在大队当了一辈子会计,算得一手好账,村里人都说他"一根筷子能算到筷尖上"。
我记得那是七零年的春荒,村里断顿的人家不少。生产队长李有才背着众人,从公粮仓里分了些口粮给关系好的几家。二舅查账时发现了这事,二话不说,骑着那辆老"永久"自行车去了公社。
结果可想而知,队长被撤了职。从那以后,村里人见了二舅就跟见了瘟神似的,都绕道走。连集市上卖菜的老婆子,都不愿意搭理他。
那时候我还小,经常听到村里人背后嘀咕:"徐长柱这人,真是六亲不认,为了个公家的账本,把乡里乡亲都得罪光了。"
"你二舅这一辈子啊,认死理,吃了不少亏。"母亲说着,擦了擦眼角,"好在你舅妈跟着他,也是个实诚人。可惜去年先走了一步。"
刺骨的寒风中,院子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咳嗽声和抽泣声。
忽然,村口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片死寂。
寒冬的夜里,谁会开车来这偏僻的小山村?
我们都朝院门外望去。一辆挂着县徽的老式吉普车,顶着风雪,停在了我家那扇斑驳的木栅栏门前。
车门"吱呀"一声打开,下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穿着一身朴素的老式中山装,外面裹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那是六十年代的老款式了。脚上却是一双沾满了泥水的黑胶鞋,鞋帮都裂了口子。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那老人几步冲进院子,直奔棺材。
"长柱!老伙计!"他一把抓起盖在棺材上的那条红白相间的土布,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嚎啕大哭,"我来晚了啊!"
这一嗓子震得院里人都愣住了。拉花圈的表叔手一抖,白色的纸花洒了一地。
我赶紧上前搀扶:"您是?"
老人抹着满脸的泪水,声音哽咽:"我叫韩铁心,是长柱的老战友,现在是县里的一把手。昨天刚出差回来,听说长柱走了,连夜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韩铁心?县长?我和母亲对视一眼,眼中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二舅生前从未提起过他有这样的关系。他总是骑着那辆补了又补的"飞鸽"自行车,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像所有老实巴交的农村会计一样,过着清苦而平静的日子。
这时候,院子外开始聚集人群。初时是几个胆大的娃娃,踮着脚尖往院里张望。后来,村里的大人们也陆续过来了,探头探脑,窃窃私语。
"那是县长吧?怎么会认识徐长柱?"
"了不得啊,原来徐会计还有这样的关系。"
"我早说嘛,徐长柱这人不一般,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
我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五味杂陈。二舅活着的时候,多少人避之不及;如今死了,又因为来了个当官的,就变了嘴脸。
韩铁心不管不顾,跪在那口薄皮棺材前,一夜未起。夜里实在冷得厉害,我给他端来一碗热茶,他却只是摆摆手:"让我陪陪老伙计吧,欠他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
村里年纪大的张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进了院子,给棺材前上了三炷香,回头看了韩铁心一眼,欲言又止。
"您有话就说。"韩铁心低声道。
韩铁心惨然一笑:"长柱这人,认理不认人。他活着的时候,从不解释自己。"
一夜未眠,天亮时分,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那些昨天还避之不及的村民,今天都换了副面孔,手里提着花圈、纸钱,脸上写满了羞愧。
老李头带着他那十五岁的小孙子,颤颤巍巍地给二舅磕了三个头。他抬起头,眼中含泪:"当年徐会计,救了我小孙子一命啊!"
原来,那是八二年的夏天,小孙子落水,是二舅跳进水库把他救上来的。老李头当时千恩万谢,可前脚感谢,后脚还是跟着村里人一起疏远二舅。
"当时我只想着跟大伙处好关系,没想到对不起救命恩人。我这心里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老李头说完,又重重地磕了个头。
出殡的队伍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韩铁心主动请缨抬棺,跟村里另外七个壮年人一起,用粗布条穿过棺材,扛在肩上。
"长柱这辈子背着的委屈,今天我替他扛一回。"他对我说,声音低沉而坚定。
从村口到山脚下的坟地,不过三里地的路程。可今天,这条路走得格外漫长。一路上,不少村民自发站在路边,向二舅的灵柩鞠躬。
走在送别的队伍里,我忽然感到一阵恍惚。记忆中的二舅总是沉默寡言,自己种着那一亩三分薄地,闲时就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捧着个搪瓷缸子喝茶,听那台老式的"红灯"收音机。
"多亏了你二舅啊。"挽着我胳膊的母亲忽然说道,"当年我们结婚,家里穷得叮当响,是二舅变卖了自己的一只金表,给我们添了三件铺盖。那表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是立功的奖励,他一直舍不得用,却舍得给我们。"
"他怎么从没跟我说过?"我有些愧疚,这些年对二舅的关心太少,每次回乡,不过是寒暄几句便离开。
"你二舅这人啊,有好事藏心里,有苦处往肚里咽。"母亲叹了口气,"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说,谁知道"
韩铁心听到我们的对话,转过头来:"你二舅啊,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死了还得靠别人给他说好话。"
趁着休息的当口,韩铁心讲起了他和二舅的故事。1960年,他们在同一个连队服役。当时国家困难,部队伙食也跟着紧张起来。
"那时候我们连队驻扎在边境,条件艰苦得很。"韩铁心回忆道,"长柱是会计,负责粮食分配。有次执行任务,我不慎踩中陷阱,腿受了重伤。长柱二话不说,把自己那份干粮塞给我,然后背着我走了十多里山路,才到达安全地带。"
"要不是他,我这条命早就交代了。"说到这儿,韩铁心的眼眶又红了。
"伤好了以后,我多次想感谢他,他却摆摆手说'革命同志之间,这都是应该的'。后来我们各自转业回地方,他选择回了农村,我去了县里工作。"
韩铁心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递给我:"这是我们当年在连队的合影,他站在第二排,左手边第三个。"
照片上的二舅年轻得我几乎认不出来,腰板笔直,眼神坚定,脸上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那时的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会在乡亲们的冷眼中离世吧。
"上个月我下乡检查工作,专门绕道来看他,才知道他身体不好。"韩铁心继续说道,"我要给他安排县医院的病床,他硬是摆手拒绝,说自己命不长了,不想麻烦人。"
想到这里,我心头一阵酸楚。二舅病重那段日子,我正忙着厂里的年终盘点,只匆匆回来看了两次。那时他躺在土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笑着说:"没事,老毛病了,你忙你的去吧。"
"你二舅发现账目有问题后,先是私下找队长谈,希望他把粮食还回来。队长不听,还威胁他。无奈之下,他才去了公社反映情况。后来那些粮食终于发到了知青手上,可你二舅的名声也臭了。"
村里的老支书低着头,脸上满是愧疚:"这事我是知道的,可当时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都怪我们胆小怕事。"
临近中午,送葬的队伍终于到了山脚下的坟地。按照村里的规矩,棺材入土前要再哭一场。可二舅孤苦一生,膝下无子,除了我们几个近亲,谁来给他送行?
没想到,韩铁心走到棺材前,"扑通"一声又跪了下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已经发黄的信封,轻轻放在二舅的棺材上。
"老伙计,当年连队给你的立功证书,你走时硬是塞给我保管。说什么'别人看了会羡慕,不合适'。这么多年,你藏着功劳,扛着委屈,今天我把它还给你。"
我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证书,上面清楚地写着"因抢救战友有功,特授予徐长柱同志三等功一次"。落款是1964年5月,那正是二舅服役的最后一年。
这时,从人群后面挤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杖。她颤巍巍地走到棺材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我是知青点的老张家的,当年要不是徐会计坚持把那批粮食发下来,我闺女就饿死了。"老太太抖着手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用红绳系着的老式"上海"牌手表,"这表是我们全家省吃俭用买的,一直想送给徐会计,可他从不收礼。今天,就让它陪着他吧。"
老太太的话引起了一阵低声啜泣。村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写满了惭愧。
一时间,棺材前堆满了村民们送来的东西:有老李头家的一瓶烧酒,有张婶子织的一双布鞋,还有几个年轻人放的几包"大前门"香烟这些都是二舅生前喜欢的东西,只可惜,他再也享用不到了。
下葬时分,风雪忽然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二舅的棺材上,像是上天在为这位一生刚正不阿的老人送行。
那封泛黄的立功证书,和村民们的心意,一起随着二舅,被掩埋在了黄土之下。
回程路上,村支书老李一路低着头,最后忍不住对韩铁心说:"县长,我代表全村向徐长柱同志道歉。这些年,我们误会他了。"
韩铁心摆摆手:"长柱这人,认理不认人。他活着的时候,从不解释自己。我记得他常说一句话:'做人做事,不求人懂,但求无愧。'"
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原来二舅早就看透了一切,却选择了沉默。
那晚,我和母亲在二舅的老屋收拾遗物。屋内陈设简单,一张土炕,一个老式衣柜,几把竹椅,墙上挂着一幅已经泛黄的"东方红"宣传画。角落里还立着那台用了二十多年的"红灯"收音机,每天早晨六点,二舅都会准时打开它,收听新闻联播。
翻开那个布满灰尘的老柜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最里层,是一个细心包裹的小木盒。我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摞摞发黄的信纸和照片。
"这是"母亲凑过来看了一眼,惊讶地说,"都是你二舅当年在部队的战友们写给他的信啊。"
我随手拿起一封,信纸已经脆得快要碎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长柱同志,我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副连长了,这都要感谢你当年的帮助和教导"
一封又一封,大多是感谢和问候,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二舅的敬重和怀念。可这些信,都静静地躺在这个木盒里,像二舅自己一样,从不对外人炫耀。
在木盒的最底层,我发现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年轻的二舅和舅妈站在中间,身边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不解地问。
母亲叹了口气:"那是你表哥啊,你二舅的儿子。六九年那年,得了脑膜炎,没熬过去。你那时候还小,可能不记得了。"
我愣住了。二舅膝下无子,原来是丧子之痛。难怪他总是特别疼爱村里的孩子,看到我们这些晚辈,眼中总是带着慈爱和些许忧伤。
木盒里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二舅这些年来借给乡亲们的钱和物,大多数都没有注明"已还"的字样。
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一句话:"人生在世,寿有长短。活着的时候,但求问心无愧;走后若有人记得,便是福分。"——写于1987年10月15日。
那正是二舅去世前一个月。
当天晚上,村里人自发在二舅家门前点起了一排排的蜡烛。那些曾经远离的乡亲,如今聚在一起,为这位被他们误解了半辈子的老人送行。
韩铁心在我二舅的院子里住了三天,亲自帮着处理后事。临走时,他对我说:"建国,你二舅一辈子活得清白,死得其所。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坚持和担当。我想请你帮个忙。"
"您说。"
"把你二舅的事迹整理出来,我想在县里开个会,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二舅活着的时候从不张扬,若是知道死后还要被人表彰,不知会作何感想。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二舅的点点滴滴:他坐在那张小板凳上,安详地听着收音机;他在田间劳作,汗水湿透了那件蓝布褂子;他在算账的时候,眉头紧锁,一丝不苟
远山如墨,近情如火。我望着那些跳动的烛光,忽然明白,人间真情不在繁华处,而在这人走后,才被看清的本心里。
如今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家人回村里,给二舅扫墓。那座不起眼的坟头上,总是干干净净的,插着新鲜的野花。村里人告诉我,这是老支书和那些曾经的知青们常年维护的。
二舅走了,可他那份"不求人懂,但求无愧"的精神,却像种子一样,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远山无言,近情无价。人世间的情感,有时候需要经历风雨,才能看清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