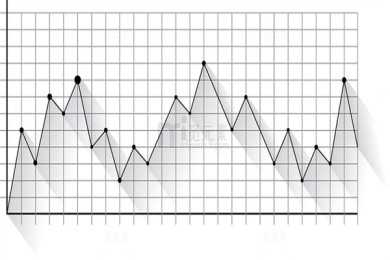七子凋零
"王大山那老头子真是可怜,办个寿酒,七个儿子一个不来!"村口李婶一句话,让我停下了脚步。
喜鹊在电线杆上叫个不停,我却感到心里一阵发堵。
我是这北方小村的人,如今回乡探亲,却听闻了这样一个消息。
王大山,我父亲口中的"堂伯",曾是村里最让人忌惮的人物。
那是1966年的夏天,老天爷像发了怒似的,半个月滴雨不下,生产队的水井一眼接一眼地干涸。
村里人端着脸盆,排着长队打水,有时候等到手发麻,才轮上自家的那一瓢。
我爹周长河当时是生产队长,按规定给每家每户分配水田。
队里那台老式的收音机里,正播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广播,父亲在破旧的小平房里,挥汗如雨地画着分地的草图。
王大山仗着有七个儿子,硬是要占据靠近水渠的那块肥地。
"不行,这分地得公平!"我爹把铅笔往桌上一拍,脸涨得通红。
王大山瞪着一双铜铃般的眼睛,盯着父亲说:"周长河,你敢不给我?"
村里人都知道,王家那七个儿子,个个膀大腰圆,村里的混混打架都不敢招惹他们。
"凭啥给你?按人口分地,你家也就那几亩地的份儿!"我爹站在田埂上,双脚像扎了根一样。
王大山咧嘴一笑,露出泛黄的牙齿:"周长河,你不给是吧?我家七个小子,个顶个的壮实,你信不信明天他们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父亲的额头上青筋暴起,但声音却出奇地平静:"原则面前,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站在父亲身后,看着王大山那张阴沉的脸,心里直打鼓。
那天晚上,王大山带着七个儿子围在我家院子里,手里拿着镰刀和铁锨。
我娘吓得抱着我哭,啜泣声在屋里回荡。
我爹穿着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衫,站在门口,只说了一句:"有本事冲我来,别吓唬妇女孩子。"
月光下,父亲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却又那么坚定。
最终没动手,但第二天分粮食,我家的口粮却被莫名其妙地克扣了。
那时候,粮食是靠工分换来的,克扣就意味着我们家要挨饿。
娘偷偷哭了一场,我爹却拍着我的肩膀说:"做人要硬气,不能欺负别人,也不能让人欺负。"
那个夏天,我家吃了不少苦头。
王大山家的七个儿子,经常故意到我家地里踩庄稼,还把我家的井水搅浑。
村里人都敢怒不敢言,都怕惹上那一家子。
记得有一次,我爹从地里回来,衣服都被撕破了,脸上还有伤。
原来是王大山的二儿子王二虎带着人堵他,说我爹挡了他家的财路。
那晚,我听见娘小声地劝父亲:"咱认个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摇摇头:"认怂了,咱周家的骨头就软了,以后在村里更没法立足。"
文革开始后,情况变得更糟。
王大山家的大儿子王大虎,成了村里的"造反派"头头,整天拿着红宝书,招呼着人去批斗"牛鬼蛇神"。
我爹因为曾经和县里的一个干部说过话,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被拉去批斗了三次。
每次回来,父亲的衣服都湿透了,头发上还沾着墨汁,但他从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一丝懦弱。
我永远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王家人带着一群"造反派"来抄我家的"四旧"。
家里那只老式的木箱被砸开,祖传的几件瓷器被摔得粉碎。
娘心爱的一对银镯子,是她出嫁时的陪嫁,也被以"封建余毒"的名义没收了。
父亲站在一旁,眼睛里含着泪,却一声不吭。
王大山站在院子里,得意洋洋地看着这一切,抽着烟袋锅子,时不时地哼两声:"这就是对抗人民的下场!"
那几年,我家过得紧巴巴的。
娘偷偷把藏在枕头下的粮票拿出来,换了几斤粗粮,省吃俭用地熬着。
我晚上做作业,只能点一盏煤油灯,那点微弱的光,照得我眼睛生疼。
而王家的院子里,却添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成了村里唯一有电视的人家。
每到播新闻联播的时候,村里人都挤在王家的院子里看电视,王大山就像个土皇帝一样,指挥着谁能进谁不能进。
我家不被允许踏入王家的门槛,只能在远处听着那模糊的声音。
父亲每次路过王家门口,都会昂着头,从不弯腰低头。
1970年的春天,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是全村唯一考上的。
父亲舍不得杀鸡庆祝,只是从集市上买了两块糖果,给我和弟弟分着吃。
他说:"咱家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这是翻身的希望。"
王大山知道后,冷嘲热讽:"书呆子有什么用?还不如我家七个儿子,地里一天能干十个你的活!"
我没有回嘴,只是更加努力地学习。
三年后,我又考上了城里的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临走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唯独王家的人没来。
站在村口的小卡车上,我看见父亲的眼中闪烁着骄傲的泪光。
我知道,这是他坚持原则、不向强权低头换来的成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城里的工厂工作。
每次回村,都能听到王家的新闻。
先是王大虎在煤矿出了事,被塌下来的煤块砸断了腿,成了残疾。
然后是王二虎因为打架斗殴进了局子,蹲了三年大狱。
王家三儿子和四儿子在分家产时大打出手,双方都不肯相让,最后两家都搬出了村子,去了外地。
五儿子和六儿子也为了一块宅基地反目成仇,一个去了东北,一个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
最小的七儿子倒是有些出息,当上了镇上的干部。
但他嫌弃老父亲的名声不好,给自己带来麻烦,索性改了姓,从不认这个家。
我听村里人说,王大山晚年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望着远方发呆。
那棵大槐树,见证了这个村子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王家的兴衰。
"自作自受啊!"李婶一边择着菜一边说,"当年他那么嚣张,现在是报应来了。"
我没有接话,心里却五味杂陈。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大山,如今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他那七个儿子,一个不在身边,真是"七子凋零"啊。
1985年,我父亲退休了,领着一笔不多的退休金,回到了村里。
那时村里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日子渐渐好起来了。
唯独王大山,住在那破败的土房里,靠村里的救济度日。
让我意外的是,父亲竟然主动去看望王大山。
"他都那样了,你还去干啥?"我不解地问。
父亲微微一笑:"人老了,什么都想开了。他现在什么都没了,惩罚已经够重的。"
昨日落日西沉,我在村头见到了王大山。
他坐在槐树下,佝偻着背,望着远方。
年近八旬的老人,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深刻。
那曾经傲慢的目光,如今只剩下悔恨、孤独和无奈。
更让我意外的是,我爹竟坐在他身边,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也在两个老人的脸上投下了时光的印记。
今天,是王大山的八十大寿。
村里人都知道这事,却没人去。
王家那七个儿子,更是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
一早,我爹拎着两瓶老酒和一些肉菜,对我说:"走,去给你王伯过寿。"
"他那样对您,您还去?"我不解。
爹沉默良久,才说:"人这辈子啊,总有明白的那一天。他现在什么都没了,惩罚已经够重的。再说,咱们村里的人,再有仇,也是一个锅里舀过水的交情。"
我跟着父亲,走进了王大山的院子。
那曾经气派的院子,如今已是杂草丛生,墙皮剥落。
王大山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桌上摆着几盘简陋的菜,一看就是自己做的。
"周长河,你你真来了。"王大山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爹放下酒和菜,笑着说:"你八十大寿,我这个老邻居怎能不来?"
我帮着摆好碗筷,三个人就这样坐在桌前。
桌上的菜热了又凉,凉了又热。
王大山的眼睛红了,端起酒杯的手在颤抖。
"周长河,当年是我糊涂啊,仗着儿子多,就欺负人"
我爹打断他:"往事不提也罢,人活一世,总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你教儿子强横,他们就没学会厚道;你教他们欺负人,他们后来连你也不念情分。"
王大山哽咽了:"儿子们都说,是我害了他们大虎残了腿,二虎蹲了牢,老三老四闹分家,老五老六为地皮吵,老七老七连姓都改了都是我的错啊!"
老人说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个曾经在村里横行霸道的王大山,如今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抽泣。
我爹拍拍他的肩膀,轻声说:"人无完人,谁还没犯过错?关键是醒悟得早晚。"
王大山抬起头,眼中含泪:"周长河,你比我强啊!当年我处处为难你,你的儿子现在城里有工作,你自己退休了也有钱花。而我呢,七个儿子,一个也指望不上。"
父亲摇摇头:"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这一辈子,从没想过要比谁强。我只知道,做人要厚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窗外的阳光洒进来,照在三个人的脸上。
我看着这两个曾经势同水火的老人,如今坐在一起喝酒,心中百感交集。
"你知道吗,我最后悔的是什么?"王大山盯着杯中的酒,喃喃地说,"是没教好我的儿子们。我只教他们用拳头说话,却没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我爹倒了杯酒,说:"现在明白也不晚。"
"晚了,都晚了。"王大山苦笑着,"他们已经不认我这个老父亲了。前年我病得要死,给老七打电话,他说正在开会,挂了就没了音信。"
我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想起了他当年趾高气扬的样子,恍如隔世。
夕阳西下,我爹拍着他的肩膀,轻声说:"岁月这把尺子,量出的都是公道。往后余生,平平安安就好。"
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您真的不恨王伯了吗?"
父亲望着远处的村庄,淡淡地说:"恨有什么用?这辈子啊,要看得开。他现在受的苦,比我当年受的还多。"
我想起了王大山孤独的背影,和他那"七子凋零"的凄凉。
"爹,您说,为什么他的儿子们都不管他了?"
父亲叹了口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教儿子们欺负人,儿子们自然就学会了自私自利。自私的人,是不会孝顺的。"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返城。
临走前,我又去看了王大山。
他还坐在那棵大槐树下,手里拿着一个旧相框,里面是他和七个儿子的合影。
那照片已经泛黄,是文革前拍的,七个小子围着他,像七颗星星围着月亮。
"当年多风光啊,"王大山感叹道,"现在想想,都是过眼云烟。"
我在他身边坐下:"王伯,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
老人望着照片,沉思了良久,才缓缓地说:"厚道二字,如今才懂。"
村口的大喇叭响了起来,播报着今年的秋收计划。
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而这个老人,却像是被时代遗忘在了角落。
我看着他苍老的面容,那双曾经锐利如鹰的眼睛,如今只剩下浑浊和迷茫。
阳光洒在他的白发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我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话:"做人要厚道,岁月会公道。"
在这个北方的小村庄,在这个静静的清晨,这句话的意义,从未如此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中。
我轻轻地拍了拍王伯的肩膀,起身离开。
回头望去,他依然坐在那里,望着那张旧照片,一动不动,仿佛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村口的小路上,我遇见了父亲。
他手里拿着一个暖瓶,说是给王大山送去的。
"爹,您真是个好人。"我由衷地说。
父亲笑了笑:"不是好人,只是希望大家都好。这日子啊,还长着呢。"
我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
不是像王大山那样,有七个儿子做靠山;而是像父亲这样,无论境遇如何,始终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春去秋来,大地轮回。
人生的得失荣辱,最终都会在岁月的长河中得到公正的评判。
这就是我在那个小村庄里领悟到的人生哲理,一个关于"七子凋零"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做人道理的永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