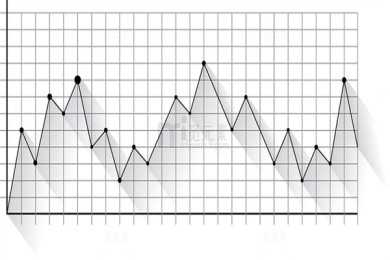牛屋内有五六个人,琉璃一看,村里的几位老单身汉几乎都聚集在这里。他们不再专注于打牌,而是以各种舒适的姿势坐着或躺着,有的正抽着传统的旱烟袋,烟雾缭绕,有的则闭上眼睛,脸上洋溢着悠闲自得的神情。当琉璃和二歪头踏入牛屋时,这些老单身汉们开始互相打趣:“哎呀,这不是老曹家的琉璃头吗?怎么突然跑到我们这牛屋里来了?”
“哈哈,这俩小伙子肯定是嘴馋了,想来混一顿好吃的。”老单身汉们的话语中充满了戏谑和调侃,但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温暖的亲切感。琉璃和二歪头面对这样的调侃显得有些羞涩,他们挠着头,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他们开始在牛屋里四处翻找,希望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老单身汉们并没有阻止他们,只是带着微笑看着这两个年轻人的举动,偶尔还会给出一些建议和指点。
琉璃走进牛屋,眼前的情景让她感到新奇。他看到七八头牛被拴在牛栏里,它们安静地站着,仿佛在沉思。牛屋的旁边是两间较小的屋子,一间用来喂养驴子,另一间则是骡子的栖息地。屋内的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那是一个用又黑又粗的罐头瓶子制成的灯,灯捻是由一根粗布拧成的,有拇指般粗细,燃烧起来像火把一样,上面飘散着一股黑烟。屋内的尿臊味浓烈,但在这股刺鼻的气味中,还夹杂着炒熟黄豆的香味。初入牛屋时,那味道刺激着琉璃的鼻腔,但当她待上一段时间后,屎尿味与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变得难以区分,仿佛成为了一种新的气息。
在牛屋的另一角,村里的老光棍黏鱼头正与几位村民围坐在一张破旧的桌子旁打牌。他们使用的是一副已经玩得油光发亮的扑克牌,那副牌的状况让人不禁联想到街边炸油条小贩所穿的围裙,同样被油渍浸透,显得有些破旧。他们说话时神神秘秘,只言片语,琉璃感到困惑,无法理解他们交谈中的含义,仿佛他们之间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黏鱼头是一个年过四十的男人,嘴巴宽阔,下颚宽广,给人一种粗犷的印象。他曾经有过妻子,但与他共同生活了几天后,妻子便悄然离去,至今下落不明。关于她的失踪,村里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们生肖相克,也有人称他虐待妻子,导致她无法忍受而逃走。各种说法都有,但黏鱼头对此一概不予理会,他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议论,只是默默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份,村里着手修建那条水渠,确保河里的水能浇地。铁头和黏鱼头之间骂大会,三言两句就直眼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铁头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黏鱼头的糗事,并以尖酸刻薄的言辞羞辱他:“韩大垒,你这个信球货,连驴和马都不如,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混蛋。”他的话语带狗子,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下面会有有趣的事儿,肯定是涉及到韩大垒,也就是鲶鱼头的隐私。村里男人女人对这事儿都感兴趣,有人开始蹿火怂恿,调油加醋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气氛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
刘铁头要的就是味道,他转向那些正在辛勤劳动的社员们,用一种带有讥笑的语气说:“你们知道韩大垒的老婆为啥跑路吗?我知道实情,因为他强迫自己的老婆去做一些张不开嘴的事情。”
村里的男人们齐刷刷盯住黏鱼头,高低不平高声低语的哄笑起来。村里人原以为是一般的夫妻矛盾,家长里短,没想到是被窝里的故事。而且,他们已经从刘铁头的话语里悟出了话里话外的意思,一定是鲶鱼头和他老婆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他们更是肆无忌惮的狂笑,那笑声让黏鱼头感到无比的尴尬和羞愧,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有人平时和韩大垒骂大会习惯了,老吃亏,今天就有了报仇的机会。他们继续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他:“鲶鱼头,你是驴吗,真是愚蠢至极,一个大笨蛋,连猪和狗都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那玩意儿,而你却强迫老婆换动作,你这种行为连牲口都不如。”
人们看笑话不嫌事儿,鲇鱼头情绪激动,与铁头发生了争执。铁头自然不畏惧,兄弟几人联手打他,鲇鱼头吃了亏。后来,村里开会聚会,红白事儿,人们聚在一起就调侃鲶鱼头,这个鲶鱼头低人一头,四处给人解释,声称铁头冤枉了他,故意让他出丑。而铁头则坚称自己所言属实,绝无冤枉鲇鱼头。
铁头进一步透露:“鲇鱼头的老婆出走后,鲶鱼头多次向我请假,声称要外出找老婆回家。我要他说实话才准假,鲇鱼头不得不向我坦白了真相。”
面对村民的怀疑,铁头发誓:“如果我撒谎,死我的当头儿子,天打雷劈我全家。”
在豫东乡村,长子长孙被视为家庭的至宝,就像皇帝的太子一样的地位,这样的誓言极为严重。铁头如此发誓,村民们便信以为真。他敢用自己珍爱的儿子的生命来赌誓,人们不得不相信。
没过多久,铁头的大儿子病死了,年仅十二三岁。村民们对刘铁头的话产生了怀疑,这事件也就没有人再提起,最终成了一个未解之谜。鲶鱼头又活泛起来,不在低人一头的活着。
琉璃和二歪走进屋内,黏鱼头咧嘴笑道:“你们两个没出息的家伙,来这里干什么?不去家里钻被窝,找你娘吃奶吗?”
琉璃不敢叫他鲶鱼头,而是很客气回答说:“大磊叔,我最近胃亏肉,想吃点肉解馋。”
他怕鲶鱼头不信,继续解释道:“你知道的,长期胃亏肉,影响我长个头。”
鲇鱼头一脸的坏笑:“想吃肉你找二歪他妈去,金格身上的肉香,上面七斤肉过瘾,下面二两肉让你解馋。”
鲶鱼头和二歪的爹陈老三是平辈儿,这样骂二歪也不出格。他一边说一边给琉璃挤眉弄眼,似乎在暗示着什么,周围的几个老光棍听了都憋不住,哧哧笑出声来。
胜利与二歪一同回怼鲇鱼头:“为老不尊,不如和这几头牲口一起吃草。”
鲇鱼头并不生气,因为他没有吃亏,看着胜利二歪兄弟俩只是干笑,仿佛占了莫大的便宜。
饲养员侯德义一边给牲口填料,一边起哄架秧子:“小破孩儿能干啥事儿,金格二两肉,老鼠洞一样,能把腿伸进去,捣蒜吗?”侯德义的话引来一阵淫笑。
他的话语中夹杂着一丝戏谑,引得在场的每个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而略带放纵。
侯德义年过七旬的,形状如一只没毛的老猴,满脑子都是整人的主意,他话不多,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拱火扇风,让双方大打出手。侯德义喂牲口多年,在村里名声并不好,因为他是个有名的老爬灰。
生产队的麦秸堆就堆放在牛屋前,那是牛和驴整个冬春季节的口粮。村里的妇女们常常提着篮子来到牛屋,偷偷地带走一些麦秸回家用作引火做饭。没过多久,麦秸堆就被她们薅去了一半。
铁头见状急了,责骂侯德义,让他看守好麦秸,否则到了春天牲口就没草料吃了。侯德义对付这类情况自有他的办法。他既不责骂也不慌张。每当有妇女过来偷麦秸,他总是默不作声,从后面悄悄地抱住对方,先是轻触上面的七斤肉,再是轻触下面的水窝窝。
侯德义很着急,他怕得罪铁头,说他干不好这份差事要换伺养员。侯德义想办法护麦秸垛,为此发生了许多尴尬难言的令人感慨的故事。侯德义是侯家家族的长辈,侄子孙子都娶了媳妇。而前来偷麦秸的人,并非是外人,而是侯德义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外姓的女性知道侯德义的坏脾气和手段,不敢轻易涉足,生怕遭到他的报复或使坏。前来偷麦秸的的人,都是他的侄媳妇、孙媳妇,侯德义对待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侄媳妇还是孙媳妇,他都一视同仁,毫不避讳地占便宜。这种行为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大家都叫他骚虎头,就是公羊种羊的意思,因为这种样不管对象是谁,它都会上。对这种绰号,侯德义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有人亲眼见过侯德义的大胆行为,看到自己的女人来偷麦秸,他不会用言语责骂自己的孙女和儿媳妇,而是直接从后面抱住腰,用他的咸猪手去触碰她们的敏感部位。这些女性在被他抚摸后,通常会感到羞愧难当,面红耳赤。她们用几句“老爬灰”责骂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但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羞耻感却难以平复。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她们往往会选择离开,以后很少再踏入牛屋一步。侯德义因此背上了不好的名声,但他的麦秸却因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再也没有人敢来偷取。这让侯德义在家族中的地位变得复杂而微妙,他的名声和麦秸的安危,似乎成了家族中一个难以解开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