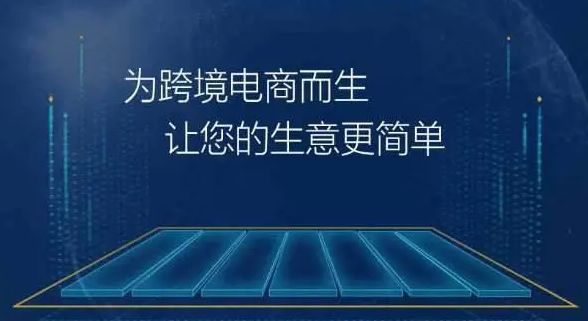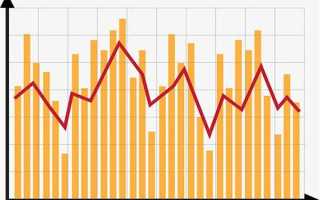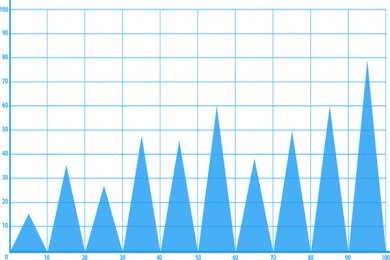“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
“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是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1]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历史却证明,每一次江山易主,国民性格也随之发生或微妙或显著的变化。
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如翩翩少年,带着与身俱来的天真,阳光而透明;又像谦谦君子,礼仪有加,文质彬彬;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如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们侠肝义胆、轻生重义、信誉重于生命,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等等,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显示着生命的挺拔和亮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壮烈与决绝。
那时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绽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绘制了一幅中华文明史空前绝后的绚烂画卷。
横扫六合,并吞八荒,视天下一切为猎物的秦始皇结束了中国人的青春期。他信奉韩非子的: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渴望利益,惧怕暴力,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驾驭天下。于是所有人都成了他“长鞭”下的牲畜,中国人的自尊、思想、群体人格第一次受到了摧残,民众的自尊,思想的自由被“长鞭”劈断,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开始成为适应严酷社会环境的手段。
很快就有人进行了实践,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嘻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这个满嘴粗话,用文人帽子当尿壶的胜利者,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再一次劣化。刘邦的成功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秦之后的中国,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成王败寇时代的开始了,春秋气质渐渐离中国人远去。幸好汉代距春秋战国不远,质拙、单纯、勇武的民风尚存,逐匈奴,封狼居胥,扬大汉天威,至东汉民气上升。
汉武帝刘彻悟出了要彻底实现皇权专制,还必须实现思想的大一统,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说秦代嬴政的“焚书坑儒”是把异见消灭于有形,汉武帝刘彻的办法则是限制思想的范围,把思想关进设计好的笼子中,笼中的鸟儿即便有翱翔的翅膀,也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内扑腾。从此统治者实现了对人的全面专制,无论是行动,还是思想都纳入了框框之中。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挣扎着试图让思想摆脱皇权专制的藩篱,重获自由,但事实证明强大的专制制度可以粉碎一切企图逃离自己控制的想法和行为。
好在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又极为深厚,特别是皇权专制的时间也还不算太久,一旦遇上一个开放的时代还可以唤醒被压抑的自信。唐代给了这样一个契机,并在盛唐时达到了巅峰,成为中国人最美好的记忆。那是一个自春秋以后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人们既不受汉代“独尊儒术”的限制,也没有宋明以后理学对思想的束缚,又较少礼法的约束,整个社会有充分的空间接受新事物,各种思想都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人的个性受到尊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文明的绚烂光华辐射四海。更可贵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恢复了阳刚、乐观、健康、自信,以李白为代表的飘逸豪放的诗风表达的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胸襟和气魄。
宋朝虽然偃武昌文武备羸弱,但面对蒙古铁骑,有誓死抗争,与家园共存亡的普通民众;有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岳飞、杨家将、文天祥这样的武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范仲淹、陆游这样的文人;有宁死不降的陆秀夫这样的文臣;还有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滔海自尽的十万军民。
元代的民族歧视和以歧视为目的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更甚的专制制度把中国人经过唐宋刚刚恢复的健康人格打入了谷底,近一百年间天朝大国的子民忍受着"末等国民"的耻辱。
沧海横流,多灾多难是这片土地的宿命,元帝国消亡了,汉人再次统一中国,却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好运。明朝以锦衣卫、东厂、西厂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在强化皇权专制的同时,更伴随着太监流氓专政以及敷衍趋势、见风使舵、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使中国人的人格再次饱受蹂躏和污染。
清代诠释了什么是一个民族的多灾多难。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汉人的自尊。剃发、文字狱、焚书、篡改历史、禁书等等在使中华文明受到严重损失的同时,也摧毁着中国人的人格。经过反复蹂躏中国人变得麻木了,麻木已然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个性之一。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人即要承受内部皇权专制对精神、肉体的折磨,又要承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残酷压榨,两座大山彻底压弯了中国人曾经挺立的脊梁,奴性也成为中国人国民性又一重要特征。
大概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诱人的职业,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频繁更迭,唐亡之后一千年间就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改朝换代之频繁为世界独有。每次改朝换代就是换了一套刑具,中国人被一次次绑上去,忍受各种刑罚的折磨,虽然有人以自绝的方式表示对新政权的不满和对折磨的抗拒,然而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屈辱地活下来。
再好的材料也经不住反复弯折,再质朴的民族,也经不住频繁的百般折磨和腥风血雨,“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残史。
在三千来年的中国封建统治中也有过无数次的揭竿而起,然而不过只是一次反对皇权专制者又成为新的皇权专制者的循环。
万年一系,是秦朝之后中国统治者的共同愿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各朝统治者所用办法略有不同:秦代创造了思想大一统的体制——中央集权制度;汉代划定了思想大一统的范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代发明了思想大一统的技术——科举制;清代创新了思想大一统的手段——文字狱。
事情还没有结束。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中期确实有几年国人扬眉吐气、意气风发、昂扬健康、主人翁感爆棚,然而好景不长,“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等接踵而至。整个世界颠倒了,一时间“牛鬼蛇神”遍地,假话、大话、谎话成了宠儿,谁敌谁友概莫能辨,“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人人自危,无数为新中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被残酷批斗、迫害致死,以运动的方式进行集体洗脑和精神催眠成为那个时代的控制术。
忍辱偷生状态下保持健康的人格只是理论家的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即使极少数意志坚定者也只能把灵魂和身体分裂,把道德与实际行动分开,“好死不如赖活着”、“唾面自干”、“退一步海阔天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等生存“智慧”越加盛行。
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被日渐架空,为适应恶劣的时代环境只能自觉或被迫地重塑自我,集体人格不断被劣化,那个阳刚、坦诚、血性、单纯、率性的中国人再也回不来了,时间久了成了集体潜意识,融入了血液,变成了基因,代代相传。
影响国民性的因素是复杂的,有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心理的等等,绝对不是从某一个方面就可以回答清楚的,但总能找到一部分原因。
正如任何一种生物性状背后都与基因有关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找到答案。
后面我将以史实为依据,从我认为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大的几个朝代做抛砖引玉式的讨论,并期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